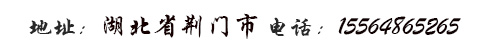李安山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
|
文 李安山 北京大学荣休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9-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 对于区域和国别研究(以下简称为“地区研究”)的方法,可谓见仁见智。有的认为多学科或跨学科方法极其重要,有的则认为这种方法浅尝辄止,缺乏深入研究。有的认为国别或地区研究过于狭隘,应该向国际或全球维度拓展,有的认为只有国别研究才能深入,有的则认为地区研究过于看重资料收集、强调现状描述,分析难以深入到位。下面以一个非洲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谈谈我对地区研究方法的看法。 实地考察是最重要最直接的方法,可以使研究者获得本土经验。虽然我从事非洲史研究以来去过非洲多次,跑过不少国家,但我对非洲的记忆仍然停留在年的加纳。当年加纳正经历一场由罗林斯领导的军人政权向民选政权的转变,我有幸住在普通人家里,在首都阿克拉见证了一些有趣的政局变革场面。白天,我坐着trotro(一种载人的小公共汽车)往来于位于市内的加纳国家档案馆和郊外的加纳大学之间,沿途碰到充斥着口号声和标语牌的游行队伍,情绪高昂的为政治立场激烈争辩的大学学生,依然照常讨价还价的菜市场顾客,无视窗外铺天盖地喧嚣声的小公共汽车乘客。晚上,我在加纳大学贾巴堂(JarbahHall)后面的小酒吧与加纳朋友们边喝啤酒边讨论加纳历史、罗林斯的为政之道以及选举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加纳师弟布鲁库姆(NanaBrukum)陪伴我到海岸角参观欧洲奴隶贩子建造的关押奴隶的地牢,并坦承地与我交流研究加纳历史的心得,加纳朋友杰米(Jimy)带着我访问可可的繁荣地恩萨瓦姆……正是在这种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的交叉过程中,我对加纳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加纳校园里,我认识了当时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历史系系主任博亨先生(A.Boahen),并有机会拜访了时任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后来升任加纳教育部长并来北京访问的拉辛先生(K.Arhin)。实地调查消除了我作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鸿沟,双方距离更近,增进了我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在加纳的实地调研还为我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各种便利。在校园里我结识了当时已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加纳历史学家科菲·巴库博士(KofiBaku)。后来,我有机会邀请他来参加北京论坛并在亚非所作学术报告。在加纳国家档案馆,我偶遇正在认真查阅档案的阿昌庞(EmmanuelK.Akyeampong),他目前是哈佛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更有意思的是,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培养的博士许亮毕业后立志从事非洲研究,希望再到美国拿一个历史学博士,后来被哈佛大学历史系录取,他的指导老师正是阿昌庞教授。我也有机会邀请阿昌庞参加北京论坛。我在加纳国家档案馆还有幸认识了当时正在为论文查阅档案的两位年青的英国学者。一位是-年欧洲非洲研究负责人、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纽金特(PaulNugent),他目前的重点是研究非洲边界与国家形成之关系。另一位是西非经济史泰斗霍普金斯教授(A.G.Hopkins)的得意门生、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主任(ResearchDirector)、经济史教授奥斯丁(GarethAustin),其研究兴趣集中在劳动力、土地与资本的关系。两位目前都是国际非洲史学界的翘楚。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有关殖民部档案时,我也遇到了不少非洲历史研究学界的朋友。我在英国伦敦的国家档案馆(KewGarden)和加纳阿克拉的国家档案馆之间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在翻阅英国殖民部档案时,经常看见一些敏感性强的档案注明“已被销毁”,但在加纳国家档案馆这种情况较少,其原因可想而知。可以看出,实地调研不仅使专业研究者有机会收集当地档案等一手资料,还可以使研究者能与当地人近距离接触而获得更加真实的感受,从而使其对一个地区人与事的理解更为直观深入,对问题的认识也会相对客观。幸运的话,还可结识更多的学界朋友,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多便利。实地考察在地区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证明了它的实用性。 跨学科研究是另一个重要方法。对这一方法也是见仁见智,相关论争还产生了一个新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然而,地区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可以通过不同学科方法融多个学科于一身,形成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一方面,地区研究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另一方面,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学科基础之上。从学理上看,确实存在“地区研究专家”。然而,一个学者的称呼或头衔总是与他的专业领域有关。例如,其博士论文突破传统汉学局限并于年创办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费正清是历史学家,将战时在押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并写成《菊与刀》而名声鹊起的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撰有《日本第一》同时又对中国问题有独到见解的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是社会学家,从研究非洲起家并以现代世界体系论而闻名的沃勒斯坦也是社会学家,通过研究拉丁美洲而提出新权威主义理论的吉列尔莫·奥唐奈是政治学家。这种跨学科的特点使得各个地区研究的学术触角敏锐,研究志趣广泛,也不断寻找各自领域的学科切入以融入国际关系。罗伯特·贝茨强调政治学理论对非洲研究突破传统语境束缚的意义。恰巴尔尝试将非洲研究置于比较政治学框架,力图提出一些有意义且针对性强的研究问题。 跨学科方法在地区研究中非常普遍,对非洲的研究尤其如此。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梅拉苏主编的《前殖民主义非洲的奴隶制度》,作者全部是人类学家。自年出版后,此书在史学界颇受欢迎。弥尔斯和考匹道夫主编的《非洲的奴隶制度》共有20位执笔者,其中12位历史学家、6位人类学家、2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对奴隶贸易的研究颇有兴趣,霍金敦和艾尔蒂斯都是经济系的。政治学家对阿非里卡人和南非黑人的民族主义研究也正在成为南非近现代史的主要课题之一。《牛津南非史》充分体现了多学科的合作。编写者中只有三位历史学家,其他包括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各方面的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1-8卷)和刚完成的《非洲通史》(9-11卷)是跨学科合作的典范,作者中除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语言学家、神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和移民问题专家等。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使得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更加紧密。 所谓地区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实际上指两个维度。一是地区研究者利用多学科方法对某一国别和地区进行研究,二是某一学科通过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形成新的学科分支(如计量史学、社会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等)。在欧洲,年成立了非洲-欧洲跨学科研究群(Africa-EuropeGroupforInterdisciplinaryStudies,AEGIS),目的是利用欧洲联盟内非洲研究机构现有的资源和研究潜力。这一机制无疑会促进欧洲大陆非洲研究人士的信息共享和学术交流,但每个研究者仍然坚守自己的专业。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非洲研究的特征之一。地区研究促进了学科整合,各学科交流互鉴方法还可涵盖各种相关理论和现实主题。例如,《非洲文学批评史稿》的题材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等多学科和多领域。专家学者集中在某一机构或项目,虽然分属不同学科,但他们对同一地区的共同兴趣、学术上的密切联系跨越了学科界限,推动了单一学科对多学科方法的应用。 比较研究是另一种值得推荐的方法。从地理角度看,这种比较可以是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也可以是同一地区不同国家的比较,甚至是同一国家内不同集团(如农民与工人、官僚集团与专业人士、草根与精英等)、区域(高原与平原、不同流域)或不同民族的比较研究。这种细化的趋势在美国早已出现。有时我们通过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来对不同地区进行比较,例如,伊斯兰教对西非和中东地区的政治代表性影响有何不同?从研究内容看,对不同地区(国家或内部区域)的同一现象的比较也非常有意思。例如,英国学者纽金特对西非地区不同国家的研究着重比较了两个法英边境地区,将税收和人口控制作为边界的因素,这些因素对殖民地国家及其后殖民地的继承者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它还说明了这些对地方行政结构、违禁品、土地使用做法的形成和归属的定义是如何产生影响的。这些在塞内加尔与沃尔特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由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非洲边疆研究网络(AfricanBorderlandsResearchNetwork,ABORNE)重点研究各国边疆地区的国计民生问题,作为这一地区研究组织的指导委员会主席,纽金特代表这一组织与非洲联盟边境计划(AfricanUnionBorderProgram,AUBP)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担任非洲联盟边境计划的顾问,参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关跨界合作议程等非洲联盟的实际运作。这种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结合值得中国学者学习。 当然,还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行业以及各种不同政治行为(如选举或竞选方式、统治集团构成、联合执政方式、民族政策优劣、移民安全)等方面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此外,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对外经贸关系日益发展,对经济发展史、工业化策略、农业制度、文化与经济行为之关系、劳工迁移和待遇、外国投资战略、土地租赁合同、国际营销策略、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等方面也可进行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比较研究。不过,地区研究与政治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比较政治的关联性最为突出。 计量方法已在各学科研究中被充分运用。以历史学为例,法国年鉴学派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从地理、社会和个人三种时间的“共时性”维度进行横向关系的研究,在计量方法的运用上独树一帜。英国社会史家与其他相关学科携手,运用数学手段和计量方法开拓研究新领域。美国新经济史学派通过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在铁路的历史作用和奴隶制的性质等研究上标新立异。对于地区研究也不例外,计量方法可为事物的定性提供数量依据,其作用是多方面的。量化数据可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最值得研究的问题上。如通过对有关资料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灾变特别多,洪水泛滥、旱灾频繁、瘟疫流行、饿殍遍野,这必然引起研究者对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重视,因为此类灾变主要是管理调度不灵、统治系统失控所致。 计量方法既可以为某种假设提供系统论证的可能性,也可以对已有结论提出挑战。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蒂里挑战工业化与社会骚动之关联的定论即是一例。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工业化意味着旧秩序的瓦解,这是一个先混乱后稳定的过程,与此相适应的是剧烈反抗运动的上升和下降,在图表显示出一条驼峰曲线。蒂里通过对相关变量的统计分析,认为传统观点站不住脚,至少法国的历史没有为上述观点提供任何可佐证的资料。通过使用计量方法,他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现象:随着工业化进程,无组织反抗逐渐变为有组织反抗,地区性反抗变为行业性反抗,并得出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这种反抗趋向组织性的过程是工业化与集体反抗之间的有机联系。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尼科里多年来精心研究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量,在非洲历史研究学界享有盛誉。他有关非洲对英国工业革命影响的著作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有的观点,“毫无疑问,大西洋商业的发展最终是英国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因素。同样,毫无疑问,非洲人及其后裔的劳动使这一时期大西洋商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非洲人对英国的工业革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计量方法还可以为地区研究开拓一些新的资料来源,对资料进行技术处理。实际上,电脑统计、心理分析、抽样技术、经济类型和计量方法正逐步成为地区研究的工具。 END 注释(完整的注释请参见原文):[1]有关非洲地区研究,参见以下文献:RobertH.Bates,V.Y.MudimbeandJeanO’Barr,eds.,AfricaandtheDisciplines:TheContributionsofResearchinAfricatotheSocialSciencesandHumanities,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aulTiyambeZelesa,“Introduction:TheDiscipliningofAfrica”,inPaulTiyambeZeleza,ed.,TheStudyofAfrica,VolumeI:DisciplinaryandInterdisciplinaryEncounters,CODESRIA,,pp.1-35;PearlT.Robinson,“AreaStudiesinSearchofAfrica:TheCaseoftheUnitedStates”,inPaulTiyambeZeleza,ed.,TheStudyofAfrica,VolumeII:GlobalandTransnationalEngagements,CODESRIA,,pp.-。有关中国非洲研究状况的总结,参见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70年述评》;李安山:《中国的非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非洲学刊》,年第1期,第-页。[2]北京论坛(BeijingForum)是经中国国务院和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北京论坛创办于年,每年举办一次,在北京举行。[3]“PaulNugent”,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aerwaduo.com/ssswddl/9080.html
- 上一篇文章: 美国为什么派这个神秘人物访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