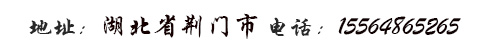追寻自由星空下的无恶之境月亮的女儿
|
精彩试读 ————— 追寻自由星空下的无恶之境 选自《月亮的女儿》 本文为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雾笼罩着整个地区,遮挡着外人的目光,仿佛是要为这块魔幻般的地方保守秘密,使其与周围的世界隔绝开来。偶尔会看到有家农舍的屋顶从雾气中隐现出来或者隐约听到牲畜丁零丁零的脖铃声,说明在这片静寂的土地上还是有生命活动。随着浓雾的逐渐散去,太阳放射出万道霞光,使挂在青草上、植物上和树叶上的露珠闪耀出迷人的绚丽光彩。那时,连绵起伏的山丘,一片片百年老树遍布的密林,一道道清澈见底的河流,东一家西一家散落着的房舍和那座天堂的心脏地带——围绕在教堂周围的苏加拉姆迪小镇便都映现出来了。设若一位艺术家来到这儿,他顿时会感到激奋难抑,面对那片奇妙的美景,甚至无力写一首诗、绘一幅画或谱一支曲子来描绘它。 玛达伦走到小河边,把裙子撩到腰间,跪下来用水罐取水。之后,她脱掉靴子和袜子,将光脚伸入水中,两眼注视着在清晨的微风中轻轻摇曳的树叶待了很长时间。每天一破晓,她就走出茅屋;是的,每一天,包括那些最寒冷或大雨如注的日子,她都要做同样的事情,把光脚伸进埃西托克河中,直至脚趾起皱,寒气顺着她的脊椎骨上升到全身,让她不停地打起寒战。许多年间,她母亲也曾跟她一样这样做。还在她刚刚学会迈步的时候,她就陪母亲去河边,模仿她的一举一动,尽管那时她的双脚还抵不到水面,只能在水面上方摇动。此刻想到这些,她不禁叹了口气。 自从最后一个春天以来,母亲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母亲了。灾难一个接一个降临到她们家中,仿佛那个叫高艾克的夜鬼将它的黑影伸展到了那间林中的茅屋之上,决心抓住猎物不放。首先是疾病夺去了小卡塔丽娜的生命。她也有几天感到不舒服,浑身发烫,同时也冷得发抖。但是一天清晨她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口渴得要命,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从那张全家人都睡在上面的唯一的一张床上,她看到父母把她小妹妹的身体用一块布裹起来抱出了茅屋。透过那扇采光和做饭出烟的大窗户,她看到父亲把小妹妹的尸体放进在栎树下挖出的一个坑里,而母亲则咬着嘴唇静静地哭泣。她看到他们在小妹妹的坟头上放了一束草本植物的叶子,然后拉起手一起举向树冠,请求古人的女神玛丽将他们的小女儿收留在她的屋檐下。 父亲不久也去世了。他患的病是高烧不退,几乎不能呼吸。母亲把一床毯子在河水里湿透将他包起来为他降温,给他喝黄花草和山毛榉树皮熬的药汤,还用荨麻束为他揉搓胸部和脊背,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那些日子,她和母亲就睡在铺了干草的地板上。母女俩在卡塔丽娜的坟旁挖了一个坑,将裹着毯子的父亲的尸体拖到那儿,掘土将他掩埋了。她们一句话也没说,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于他们的生命来说,死亡没有什么奇怪,倒不如说死亡是他们旅途的伙伴。但是她的母亲再也难以从那种打击中振作起来。玛达伦看到她身体一天天垮下来。她几乎不说话,坐在火旁的一条长凳上,或者坐在茅屋前的一块大石头上,那石头是昔日生活在林中的某个巨人忘在那儿的。她坐在那儿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个不仅埋着她的丈夫和女儿,而且也埋着她的父母以及她父母的父母的地方,就是那棵神圣的大树下。 玛达伦重又叹了一口气,把脚从水中拿出来,那双脚不仅起了皱,而且由于寒冷而呈现出紫色。在登上靴子之前,她感到双脚穿上厚厚的羊毛袜子非常舒服。然后,她抱起水罐,回到了茅屋。 她母亲已经把锅坐在了火上,正在慢慢地用一把大木勺搅动猎,但父亲却是一位用陷阱或机关狩猎的行家。 “森林是属于大家共有的。”在有人提醒她父亲没有修道院院长的明确准许而私自捕猎会带来的危险时,他这样反驳说。“在这儿还没有修士之前,我早就在这儿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修道院院长任命他为护林人。他的任务是防止别人干跟他同样的事,即在修道院的田产上狩猎。同时他也负责发现狗熊或某群狼的到来,及时通知修道院院长。那时院长便命令镇子里的人跟随他们出动,尽义务把打来的兽皮交给他。这位护林人还要负责不要让任何老树倒进埃西托克河或奥拉维德亚河里,或者杂草和石头堆积起来阻止河水正常流淌。作为报偿,他可以在林子里随便打猎和砍伐家中所需要的烧柴。 埃斯特瓦尼娅没有让外人知道她的丈夫已经过世,因为她知道,一旦修道院院长知道她丈夫不在了,马上就会把她和她的女儿赶出家门。院长不会有兴趣让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占据那间茅屋。他会毫不客气地把她们赶走,不问她们将来如何度日,而让另一个家庭住进去。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她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和母亲就险些失去那个栖身之地。她和农夫华内斯·德阿斯皮奎塔的结合使她避免了被赶出家门。然而现在没有任何华内斯来代替另一个华内斯,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拖长时间不让圣萨尔瓦多修道院院长得悉她的丈夫已经离世。暂时她们还可以过安宁的日子,但是,以后呢?以后她们将怎么办? “妈妈,你好?” 玛达伦的声音把母亲吓了一跳,她甚至没听到女儿抱着水罐进来。她转过身去,静静地审视着女儿。尽管女儿身材矮小,但她已经是个女人了,可以生儿育女了。也许该是给她找个伴侣的时候了。那样,设若运气好的话,她们的茅屋里又可以有一个男人,让修道院院长高兴了。那样她们就可以不离开那间茅屋,也不离开她们家的亡灵了。只需找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就行了,镇子里有一些人家的小儿子也正在找姑娘结婚哩,哪怕姑娘不是土地的继承人。那些小伙子们想,找到个姑娘结婚,最坏也可以有活干了,有地方住了,也就再也用不着为一个哥哥或随便什么另外的人干活了。埃斯特瓦尼娅想到了桑西奥,他是铁匠的第四个儿子。那孩子不是太机灵,但只要勤劳也就可以了,他可不是懒人。他的外貌也不迷人,恰恰相反,两道眉毛连在一起,身材又矬又胖,但是,她知道他人品忠厚,性格脾气好,这种品德比长相要重要得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埃斯特瓦尼娅先是吩咐女儿把家务事全部做好并且到河湾处看看有没有杂草和树枝堆积堵塞河道,然后便向镇子里走去。走时她还告诉女儿她要到中午才回来,但没有告诉女儿她是去找铁匠和他的妻子商量要她和他们的儿子结亲的事。一般来说,他们一家人每周都去苏加拉姆迪,但是自从父亲去世以后,四个月了,她们娘儿俩都没去过一次。玛达伦没问母亲去干什么,只是按照母亲的吩咐去干活了。到了下午后半晌,她开始有点为母亲的迟迟不归担心了。她走出茅屋,爬上小山丘,远远向镇子张望。她在小山丘上待了很长时间,一边把她的长发解开辫好,辫好解开,一边巴望着看见母亲的身影出现。已经感到有些秋意了,树木开始落叶,夜晚降临得早了,微风中夹杂着潮湿和烧焦的木柴的味道。她听到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告知人们第二天是礼拜天,她脸上露出了微笑。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母亲才迟迟不见踪影,不回茅屋,而是直接去参加聚会了。这样一想,她便从小山丘上跑下来,往山洞走去。 山洞那儿寂静得出奇。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周围只有她一个人。随着她走近洞口,那寂静就越发的深沉。看不到驴子,也看不到车子。听不到人声,也不见有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她以为自己搞错了,但像每个星期六一样,教堂的钟声在叫人们去做晚祷了。绝对不会错。可是,为什么不像从前一样此时这儿会来了许多人?她走进山洞,没有人点起篝火把聚会的地方照亮,洞中烟雾腾腾,墙上映出长长的人影。风从山洞巨大的缝隙里吹进来,呼啸声跟穿过山洞的小河的流水声混在一起,奏出一只轻轻的死亡的曲调,她感到一阵恐怖。玛达伦吓得魂飞魄散,拔脚跑出山洞,一口气跑到家中才停下来。 她产生了幻觉,总感到身后有一些穿黑衣服的人带着逼视的目光在追赶她,所以她拖了很久方入睡。夜间她几次在黑暗中摸索着在干草垫子寻找埃斯特瓦尼娅的身体,但后者睡觉的地方是空着的。她没有力气起床,困得睁不开眼睛,她又入睡了,但还是感到一次又一次地被一些无形的幽灵所围绕,那些幽灵将她包围在比夜晚更黑暗的圈子里。 她终于醒来了。感到有一束阳光照耀在她的脸庞上,她一跃而起从床上跳下来。除了小妹妹死亡、她的高烧消退那一天外,她从不记得有哪一天醒过那么晚。她看了看熄灭的炉灶,希望看到母亲在那儿准备早餐,但是她没有回来,于是一阵恐怖又袭上了她的心头。肯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母亲从未夜不归宿过。即使去为人守灵或去照顾产妇她都不会整夜不归。她总是回来把家中的人叫醒,哪怕然后又重新出门。玛达伦用罐子里还剩下的一点水洗了洗脸,然后便走出家门,但是这一次她没有去河边,而是朝苏加拉姆迪走去。 跟前一天黄昏在山洞那儿一样,镇子里死一般的寂静,门和朝外开的木板窗全都紧紧地关闭着,街上不见一个行人。后来她终于碰到了一个人,那人本来跟她见过面,但此时却故意垂下了眼睛,走到她近前时加快脚步过去了。她敲了几家的门,但都没有回答。甚至连平时总是大开着的教堂的门现在都关着。正当她开始绝望的时候,她听到有个人在轻声叫她的名字。她环顾四周,好不容易才看到了她妈妈一个叫西蒙娜的表妹在向她打手势。 “怎么……” 她的话还没有问完,那女人便扯住她的一只胳膊,把她使劲地拉进家中。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疯啦?”西蒙娜以让她吃惊的口气对她说。 “我母亲……”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西蒙娜像是发火了,但她不知道西蒙娜为什么要发火。 “埃斯特瓦尼娅被捕了。” “被捕了?为什么?” “说她是女巫。” —转载授权、商务合作— 联系邮箱:anyuzhu cctphome.北京看白癜风效果好医院北京哪能治好白癜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aerwaduo.com/ssswdfj/698.html
- 上一篇文章: 事业单位考试公共基础知识每日一练201
- 下一篇文章: 科普这些图带你看懂世界航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