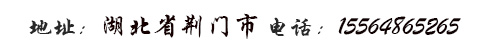我生命中的星辰sect女孩
|
沈阳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bdflx/171107/5824583.html叫她Grecia。 站在《一站到底》波士顿赛区明亮的舞台上,穿白裙的主持人郭晓敏问我是否还单身,我点头承认。接着,她问我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我说,“没有标准,只要喜欢,女孩儿也可以。” 台下的观众一片哗笑。 比赛结束后,朋友们对我说,观众不该笑我的。我想半天,才反应过来她们指的是哪件事。那不是真正的笑,我根本没有上心。 狩猎社会后的数千年里,多数女性退居到男性的社会地位之下,活在男人的眼里。如果不能往上走,就只能往下走。如果女性不能在社会不同领域的客观进步上产生竞争意识,就不能实实在在地互相欣赏、心悦诚服。情绪无处安置,就衍化出了排斥和嫉妒。喜爱与嫉恨本是不同环境下产生的同一种情绪。人与人之间的爱,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透过那源于不理解的笑,我想起了一个人真正的笑声。那是欢笑、是发自肺腑的笑、是让人心驰神往的笑,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大笑。那笑意穿透我的每一个细胞,长存在我的记忆里,令人每时每刻只要回忆起,都能够愉悦地笑起来。 我心中有这样一个女孩儿,如果说这世间有一种美德叫做快乐的话,她便是这美德的至高点。她的名字是Grecia,我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想她。 (圣萨尔瓦多山上的合影) 那是我最开始尝受人性挣扎之后,她无意间把我从漆黑的深海里打捞出来。我看见她,仿佛看见一束刺眼的阳光。就像无数行在黑夜里向往白昼的人一样,我从这样一个快乐的人身上汲取了真正的光亮。 那是大三的七月,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青年代表,我在和平之船上遇见她。起初,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对方。我是个敏感悉心的东方女孩,她是个热情奔放的西方女孩,我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心中拥有一个世界的人,是很难注意到外界的。 那时我的心中忧郁而宁静,而她的世界里洒满了欢乐,潜意识将我们隔开。我曾经也是个满世界都是快乐的人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意识到了她的存在。 也许是她在舞台上演讲得挥洒自如,那么自信,那么地自信,就好像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说话能比得上她。下台后,我问她,怎么能不用演讲稿?她惊恐万状地用手捧起脸反问,“怎么能用演讲稿?演讲拿稿子我会紧张得讲不出话来的啊!”是啊,她就是那么自信啊。 也许是在船上KTV厅的聚会,她迈着欢快的舞步,靠近了放不开的我,教我怎么挪动步伐,让我融进节奏的鼓点。“Cindy,看,向左移动三步,再向右移动三步......对,对,就是这样!”她将我交给帅气的墨西哥男生Ado跳舞,任他夸我跳得有多尽兴、有多好看。 也许是在尼加拉瓜的海边小镇时,几人跑到了镇上最大的舞台上即兴跳起江南Style,全镇人都来围观。只见她一边跳一边笑,双手摇动如摇铃,发丝飞扬在风中,仿佛满天的星子都能听到,听到了都会为她掉落下来的。她的话语流溢出生命的活力,“没有舞蹈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了!” 乐声如此鲜明,我心中再也无法平静。 (在圣萨尔瓦多活火山山口) 她注意到我,是由于同行的两三人夸我又会摄影,人又上镜,夸了一路过来。行程的倒数第三天,到萨尔瓦多,Grecia终于小女孩似的抱怨了一句,“我也挺好看的呀。”我这才开始直视她,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Grecia赶紧笑着将手机塞进我手里:“他们说你拍得好,可以帮我拍一张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开始一边指挥她摆动作,一边寻找最好的角度。她又笑了:“随意一点拍就好了,我没那么在意的。” 她在我的镜头中,我的眼里有了她。她笑得那么自在和肆意,是真的很好看,他们绝对不会说她有多好看。 原来,我也是可以如此欣赏一个女孩的啊。 可我是个女孩,要怎么去爱一个女孩? (祈雨仪式我拿着花) 第二天,我们参加了一支阿纳华克族印第安人祈雨的舞蹈,酋长说,“舞蹈有如梦境,人跳舞的时候,会和大地紧密地联系。” 酋长说,在古老的世代,他们的族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走遍整片大地。语言不通,但心灵相通,旅行者被认为是神圣的,他们无畏地传播知识。旅行者会将花带在身上,因为花是这世间最美丽的事情。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Nimesdesuda’,意思是‘我爱你’。 “花代表我的爱,将我摘的花带到你去往的地方吧,我就会一直在你身旁,我们不会分开。将花传递下去,幸福就会传递下去。” 酋长问谁想要花,我举起手。他送给我,对我说,“你一定要相信魔力。” 转身,他让所有人围成圈,“去寻找你是谁吧,你就能再次带领我们,你就能控制好你自己。没有好坏,只有能量。” “跟我喊Compassion!”他对天高呼。 我们一群人手牵着手,一齐呼喊这个意为同情的词语。 “所有人伸出手,跟我喊Compassion!”他朝天仰头。 所有人都将手举向天上大声高喊,去感受这个象征着雨水的词汇。 ...... 不一会儿,万里晴空奇迹般地下起了瓢泼大雨,也许只是巧合。但相信巧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匆匆上车,我第一次坐到了Grecia身边,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谈话。我对她说,“我要把这朵花带回纽约,做成标本送给你。”她特别高兴,我们都很高兴,人与人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了。 我小心翼翼地将花放在车上,将它带回旅馆,找到书夹了起来;后来上飞机时,我把它护在手中,捏出汗来;等到回纽约后,方有机会做成书签。不过这都是后话。 (给她做的书签) 为什么总要到旅程的最后一段,才注意到重要的人? 坐在车上,我们二人兴奋地聊起刚从酋长那里获悉的有关死藤水的传说。这是一种藤蔓和叶子做的饮料,会给人带来濒死体验,将感受充斥人的身体和指尖。据说,它打开人天眼,能净化人心灵,将人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们颇有兴味地议论着,都说以后想去秘鲁试试。 大雨不愿停歇。 车辆抵达了圣特克拉镇,在市场巨大的顶棚下,我们听着隆隆的雷雨,品尝烤鱼,醉酒欢笑。吃完后去逛街,天气炎热,一行人在雨中散着步,丝毫不在意被淋湿的衣服。 首饰精美而廉价,我买了一串形状不规则的蛋白石手链,Grecia买了一副流苏耳环。 先逛完的人先去酒吧避雨,我跟在她身后。酒吧上方放映起了最新流行的Despacito,她随意地跳起舞来,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Despacito是她最喜欢的歌,这首歌的意思是感情太快,请你慢一点的意思。可是,你看——一旦跳起了舞,她就根本慢不下来,她的口中哼着歌词,以最快的节奏舞动着双肩,挥舞着双臂,挪动着脚步。是欢情的舞姿,是飞扬的流苏,是急促的鼓点,她与音乐浑然一体,与舞蹈融为一体,与生命不可分离。 像是在舞池中央跳舞,那是烧灼着生命的、洋溢着自信的舞步,像是在世界中央唱歌,那是击碎一切黑暗、打破一切秩序的歌声。不,文章根本无法描述她,她应当存在于最绚烂的诗歌中。 她是快乐的源泉, 她是自由之风, 她是爱情。 (为Grecia拍的第一张照片) 明明已经到旅行的最后一程,就要相安无事地结束了。可说起来,也不怕你笑:在萨尔瓦多女权主义之家的最后一夜,我做起了莫可名状的梦。我梦见她身穿淡粉色的丝绸睡衣,周围气氛一片旖旎的瑰红,拂过窗帘的是夏季闷热的风。但是你瞧,我连动都不敢动,在梦中我胆怯地低着头,悄无声息,掌心微抖。 惊醒后的我对自己的梦境不敢置信,想要赶快下楼去喘一口气,去吹一吹热带午夜滚烫的风。竟又瞥见了她,是真实的她,半夜还在和家人打着电话。她总在和家人打电话。我有点不知所措,两只腿不知往哪儿迈,走向大门口,又折了回来。 我去倒了杯水,坐在沙发上喝。等她打完电话,上前请求她给我推荐她最喜欢的西班牙语歌。她认认真真地打出了几首歌:NataliaLaFourcade的HastaLaRaíz和TuSiSabesQuererme、Lambada......“都是舞曲。”她说。她推荐的歌可一定要听听——只凭想象,就能想象出这个女孩儿有多快乐了。 听着她的声音,我的心思又不知道飞往哪里去了。我想着,能和一个你爱的人一起旅行两周,你自己还意识不到,一切都表现得很自然的时候,是多么幸福的恩赐啊。 在萨尔瓦多最后的这个夜晚,是想象不出的美好,在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在乎别人在做什么,根本不在乎尽头指什么。只想永远这样坐着、坐着,聆听夏夜的蝉鸣,任悸动的晚风,透过窗户吹拂着面庞。 (圣萨尔瓦多玫瑰经教堂的耶稣像) 最后一天,有人先行离开,有人留了下来,想在萨尔瓦多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做最后的旅行。Grecia答应带我和她的本地朋友一起游玩。 有一名女孩子问我Grecia还带不带人,我立即摇头。“当然带了,一起就好了!”Grecia看见了我们。嫉妒——是啊,我竟然产生了这样的情绪。嫉妒,却因她浅尝辄止,片刻烟消云散。 车上放的音乐是Despacito,她顾自唱着摇着。忽然她转头对我说,有一次她去见她最好的朋友,没有通知,想要给她的朋友一个惊喜。她的朋友见到她时果真欣喜万分,和她喜悦地拥抱在了一起。是啊,我不是特别的,她一定有很多朋友。 然而她感受到了。 到了机场,我喊住她,解下手腕上我在圣特克拉镇上买的这辈子见过最喜欢的手链,就是那串蛋白石手链,给她戴上。 她对另外那名女孩子说想跟我多呆一会儿,让她先走。我俩用旅程最后的两三个小时,在电脑上一起看了《怪物史莱克2》。 我回纽约实习,她先回一趟墨西哥再到纽约开会。Shermin安排她跟我住在一处。几天后,Grecia给我带来了一串她和她的哥哥在墨西哥城为我挑选的手链。两排蓝色的石头不规则地串在金色的丝线上,蓝色耀眼的石头中好像闪烁着璀璨的星辰。再喜欢的私藏,也比不过一份从他人那里得来的礼物。我如获瑰宝。 我们一起去联合国参会。她代表和平之船参加了联合国高级别政治论坛,在总部的会议上发言。午后,我拎着菠萝饭在路边等她。“Cindy,派我去的人批评我,说我不应该自作主张上台发言。”她委屈巴巴地对我说。“没关系,别去想,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损坏后的手链) 每天晚上,她都会和家人打电话,我在一旁忙我的实习工作。 打完电话,她总会抱着一个粉红色的抱枕睡觉,上面画着迪士尼的各个公主。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带着这个枕头了,她说她有一个公主梦:“我对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是有很多要求的。我的男朋友必须会说西班牙语,不然怎么能跟我的家人沟通呢?他还一定要对我好......” 白天,我们两人一起去了时代广场上的迪士尼商店。看到商店里满天的孔明灯,她向我推荐了《魔法奇缘》,后来这也成了我最喜欢的电影。 我们在时代广场上的洋红意大利餐厅用餐,点了一大盘炒鱿鱼。点餐的小哥是墨西哥人,见她就问,“我能不能娶你?”我和她两两相望,哑口无言。看我们沉默,他转身走了,Grecia这才抓着我迸发出大笑,我也笑了起来。 我们的饮料上各有一颗樱桃,她问:"Cindy,你会不会用舌头给樱桃枝打结?"在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时,她就把樱桃枝放进嘴里,打成了结。我试了半天也做不到,只是嚼碎了蜜饯的樱桃枝,嘴里甜滋滋的。你看,这姑娘啊,坐在哪儿都能想到好玩的点子。 很快,她回墨西哥了。 后来一年的时光我是和Shermin一起度过的,在纽约这片地方,我感受了她的幸福、她的悲伤,产生了长久的情谊。随着感激她帮助我和自己爱的女孩有过一段时光,对她的感情亦充盈、照亮了我的胸膛。 (用舌头打结的樱桃枝子) 所有常用的东西都是会磨损的——双线的手链断了一根,就好像断了一根心弦。我将损坏的手链继续戴着,但过了半年,手链的另一半也断了。宇宙色的石头如泪珠滚淌一地。我安静地把一颗颗小石头和已经磨损黯淡的丝线收好,带回国内的家中,放进了抽屉深处。 Grecia在加州工作了。我给她寄过一次生日礼物,附上了一封用桃花纹案的古典信笺和西班牙语写的信。书写时,手中的笔写每个字都恂栗着。 “嘿,Grecia。”我的手停住了。 “嘿,Grecia,你还好吗?” 我写了几行又重新换了张信纸。 “嘿,Grecia。”这回字迹平稳了些: “希望你在加州一切都好。自我们上次相见已经过去一年了,但我还是常常会想起你,以及我们在和平之船度过的快乐时光。” “生活是如此美丽,每当我听到Despacito这首歌时都会想起你,我记得你是如何让我从沉寂中快乐起来的。好希望不久以后还能再次见到你。我永远都是你的朋友,无论我去往哪里。” “祝好,Cindy” 半年杳无音讯,可能是邮递员太慢了,也可能是她又去其他地方给别人带去欢乐和大笑了。 半年后才收到消息:“天呐,Cindy!我收到了你的礼物,非常激动。无论你到哪里,我都会在这里支持你!” 又是那么、那么快乐的样子。还好——还好依然是无忧无虑的那个她。也许,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会回到她身边吧。一天,一天或者两天就好。 又有两年没联系了。 我不敢联系她,那样至少,我和她之间的每个回忆都是美好的。交集少不代表喜爱少,我珍惜过我们一起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时间。 (联合国拍的照片) 有这样一个女孩儿,她很美,是从灵魂深处散发出的美,她拥有我能想到的所有美好的词汇。 有这样一个女孩儿,她周身流溢着光芒,是我的心之所向,神之所往。她让一个古典的东方女孩,爱上墨西哥淋漓尽致的文化。 有这样一个女孩儿,她太热烈,太耀眼,太让人不敢肖想。她太热烈,我害怕快乐满溢出来。她太耀眼,我只能选择远离或者奉献。她太让人不敢肖想,我生怕给她带来任何影响。多好啊,多好啊,她值得这世间最好的一切。 好开心啊,只要一想到她,我就好开心。你也能像我这样开心得满脸欢笑吗? 她的名字是Grecia,她的名字是西班牙语里的希腊,我总以为她的名字是恩典。 叫她Grecia。 她是快乐, 她是快乐的恩典, 她是这世间快乐的源泉。 文章已于修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aerwaduo.com/ssswdfj/6270.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日一测教资打卡727
- 下一篇文章: 颐养会,全岛全龄人的健康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