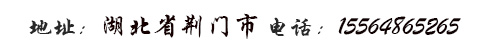浮城纪行台湾亚细亚的孤儿
|
“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巨流河》今天,我们不吐槽,因为历史早已经千疮百孔。↑日据(治)时代的残迹→黄金神社亚细亚的孤儿 文/嘉木 九份,金瓜石,基隆风雨孤舟“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悲情城市”——九份 年,后来成为台湾音乐教父的罗大佑,在他的第二张专辑里推出了《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台湾的命运——便像这歌词所叙说的那样——如同被放逐到茫茫太平洋上的飘萍,交杂着各种颜色、各种方向的风,却惟独失去了根。在台湾的“中国人”——这对他们来说,多少是一个辛酸的称谓。蒋介石退守台湾之际,曾立碑“勿忘在莒”,扬言要“反攻大陆”,然而多少年过去,面对和平的大势所趋和岛内的复杂局势,自身认同尚且面临危机的“流亡者”们,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也许是演绎这份离散之情的经典之作。基隆林家兄弟在乱世的悲剧境遇,以及在台湾人心中抹不去的“二·二八事件”的伤痛,都在其中呈现。而作为电影外景拍摄地的九份也由此驰名。九份位于新北市瑞芳区,日治时期因为盛产金矿而鼎盛一时,大批淘金者涌入,将这里的坑道挖得如蛛网般密不透风,曾有“小香港”和“亚洲金都”之称。然而我们到达九份的时候,这里早已脱去了旧日繁华的外衣。一行人登上金瓜石的黄金神社,只见荒废的基座和孤独的石头鸟居,曾见证日本的统治与“黄金山城”的繁荣。天风猎猎,世事沧桑,吹散了历史再也无法聚拢,而人来人往之地,喧嚣终究归于平静。财富与欲望枯竭之后的九份,终得以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 黄金神社?九份山城当然,闻名而至的旅人仍是不少的。在九份的盘山公路上,随处下车,便能钻进一条熙熙攘攘的巷子里,领略昔日山城繁华的余音。台湾小吃甚多,这里的巷子便是明证,芋圆、肉干、蚵仔煎一应俱全,不仅如此,在上上下下的坡道两边,也遍布许多颇有韵致的创意铺子,贩卖些古早的“台湾特色”,一瞬间将人带回到那个传说中的年代。于是好玩的,好看的,莫不齐全,在城中小巷游荡的过程本身也成为一种眼福。偶尔撞见老戏院的院墙上民国风的壁画,或是电影镜头里熟悉的酒家之时,则似时空易位,充满了错愕感。 九份闲逛,也可以有别样的味道。比如偏离人群走上一条清静的小巷,在一草一木间寻访生活的辙印。九份民居多沿山而建,远眺近观景色俱佳。狭窄的小道两旁各是风格不一的小楼房,一路走下去,好像穿行在另一重天地。在一处简陋的别墅之处,我邂逅了一只白猫。暖暖的午后,她本来趴在石梯上晒太阳,另一只小伙伴也在附近张开手脚,躺在高处的阳台酣睡。淘气的“弟弟”、“妹妹”则与经过的游人们嬉耍,摆出各种姿势和镜头捉迷藏。我们路过时,猫咪方才懒洋洋地伸了下胳膊腿,回头一瞥,慵懒的眼神让人捉摸不透。 ↑一只白喵↑基隆港。有天津卫的味道 齐邦媛先生在她的回忆录《巨流河》一书中,曾记载她们一家迁台之后,自己屡次去基隆港接船的经历:“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 前些日子吴宇森大作《太平轮》上映——戏如何且不论,至少让那段特殊时期的乱世情愁重回华人世界的视野,而基隆港,作为国共内战后期用于国军眷属撤退的接站港口,也被迫来到了聚光灯的舞台中央。 有人把基隆比作北美的NewYorkHarbor,然而对于台湾的外省人而言,基隆却并不完全是新大陆的开端——毕竟,相对于扬起自由旌旗的雄心勃勃的美国人,台湾人却是以逃亡者的身份赶赴基隆的。对他们来说,这里是暴风骤雨的短暂终结,也是漂泊旅途的漫长开端。 如今的基隆依然是一座人口众多的热闹港口,亦不乏令游客心驰的景点,譬如让吃货垂涎三尺的庙口夜市,和西北方15公里左右的野柳地质公园。然而要一堵其人文意蕴,却不得不亲自走入这座城市的街巷里弄里探索。漫步于基隆的大街,会逐渐感受到它和临近的台北的迥异之处。 在市中心耸立着诸多西式风格的建筑,构成了一条带着浓郁怀旧气息的长廊景观。作为开放的港口,这里似乎与西方人的关系更密切。最初在此地殖民的西班牙人,早在年便在今日基隆的和平岛(那时称社寮岛)修筑“圣萨尔瓦多城”,后来基隆则历经荷兰人、郑氏王朝、清王朝、日本人的统治。可以说,在台湾的历次易主中,基隆都首当其冲,这也使得港口以片瓦之地承载着数百年权力更替的腥风血雨,同时也留下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强烈印迹。夏日午后,任意徜徉在一字排开的小洋楼之间,颇有一种离了宝岛,重回天津卫的感受。于是想到年的八国联军,也正是从天津港登陆,一路烧杀劫掠,攻陷北京。近代中国的港口城市,在表面的繁荣背后,颇有同样不可告人的心酸郁结。 Taipei,HeyTaipei台北往事“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直面历史你有没有胆?从基隆往内陆几个小时的车程,便可抵达台湾的心脏城市台北。如今的现代化和繁华景象早已掩盖了当年作为“化外之地”的偏僻与荒芜,在以铜钱为“图腾”的台北大厦附近,你会以为自己恍如身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腹地。车水马龙的罗斯福大街与热带树木相互掩映,灯红酒绿的夜店文化也使“暖风熏得游人醉”,在没有限行的台北街头,机车的咆哮声激发着市民雄心勃勃的荷尔蒙。可以说,台湾再无一座城市拥有如台北这般的自信与强力,就算在仅次于它的第二大城市高雄,也决计找不出台北东区一样的“花柳繁华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台湾人在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奇迹之后,在一系列的经济腾飞中,多少已经淡忘当年留下的历史疮疤。然而物质的富足却始终填不满灵魂的虚空,命运离散的残缺无法用摩天大楼来补齐,于是对当代的台湾人而言,“传统”一词对他们反更显得弥足珍贵,这就使得即便在台北这最为富庶的都市里,也还保留着足以令人抚今追昔的凭证——譬如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天下为公大王椰子你说厦大也有椰子树诚品信义店夜街头 说起“故宫”,若我们只能想到紫禁城那血红色高墙围成的故地,那必定是不完整的。年江山易主之际,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也顺手牵走了旧故宫中大量的无价之宝,譬如被誉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毛公鼎”,曾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引起我们无限遐想的“核舟”。这些文玩珍宝的故乡,无一不在海峡彼岸。也可以说,正是被赋予了强烈历史印痕的古物,让尝尽离散之苦的台湾人始终不忘自己的文化身份,决绝地挺过了与美断交、失去联合国合法席位、 势力掌权等一系列风云变幻,执着地坚持着身为炎黄子孙的那份骄傲感。“故宫”之于台湾的中国人,便如同“约柜”之于漂泊四方的犹太人,只要还有一息尚存,便绝不肯放弃自己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断作大小两段,又在近代的历史风云中各自纷飞,前段《剩山图》陈于浙江,后段《无用师卷》藏于台北。年6月,两幅传世画卷于多年隔绝一水之间后,于台北“山水合璧”,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这样形容这一文化之盛事:“画是如此,人何以堪。”对于依旧天涯漂泊的中国人而言,不知听闻此语,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感慨了。(嘉木) 吹散的天风再难聚拢 Tips:这,其实只是台湾游记的下篇,之所以先发下篇,是因为小编不知道诸位观众能否接受上篇的尿性。回复“台湾”,可以获得《宝岛与海》——我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欢迎随意吐槽。圖城志CIVITAS喜欢这个公号的话就按住下面的儿童白癜风有哪些症状北京看白癜风疗效好专科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aerwaduo.com/ssswdgk/110.html
- 上一篇文章: 这个几乎看不到亚洲面孔的七彩国度,
- 下一篇文章: 全世界第一所正规的聋人学校于1755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