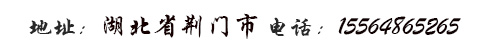论文项文惠近代地图中的台湾景象及其变
|
研究白癜风的专家 https://m-mip.39.net/news/mipso_5941620.html 1引言 对中国台湾历史地图的利用表现在整理并出版地图集[1,2,3,4,5,6,7,8]两方面。研究则集中在四个层面。第一,发展历史。夏黎明梳理清代台湾地图绘制的脉络,分发轫期、巅峰期、衰退期、转型期四个阶段,政治、兵备、行政管理之需,是影响其种类、数量、内容和品质的主要因素,促成了不同阶段的特征[9];钟美淑考察中国台湾地图测绘的历史,分为入清版图以前、清代、日据时期、光复以来的测绘四个时期,并阐明了各时期的特色及价值[10];林惠娟等在叙述中国台湾地图绘制发展历程时,又研究了其出版、收藏以及数字化[11]。第二,绘制方法。夏黎明认为山水画法、计里画方法是清代台湾地图的主要绘制方法,数量至少在70%以上[12]。第三,图例符号。图例符号用在表达空间内的地理信息,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洪明宏分中国台湾地图为清朝、日本、民国三部分,把地图上出现的视觉符号汇集成表,以此判断、推测主政者包括当地居民的环境思维[13]。第四,内容价值。ChristineVertente等通过地图,叙述了中国台湾的沧桑历史[14];赵大川用21幅古今地图,论证了中国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终将回到祖国怀抱[15];呂荣芳在考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藏《清初手绘台湾地图》展示的行政设置后,分析其绘制年代、性质和意义[16];许维勤在辨析《清厘台属汉番边界地图》绘制年代、用途、作者时,凸显其对研究土地开发、土地权益、边疆、防务的史料价值[17];金卫东考证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幅清代台湾地图[18];周运中以新发现的《皇明职方地图》下卷之《万里海防图》,确定了鸡笼(基隆)、淡水、北港等的位置,进而以明代《福建海防图》上的22处台湾重要地名,证明中国台湾在明朝时不仅属于福建管辖,而且绘制出完整的台湾地图[19,20];陆传杰利用史料、古地图以及田野调查,在地名与族群典故、地形证据的推理和辨别中,挖掘了背后的故事,更正讹误的地名[21];许毓良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淡水厅舆图》(年)、《拟布澎湖水陆各要隘水旱雷图》(年)、《凤山县地图》(年),说明了中国台湾的军事现代化始于清法战争[22]。 综上,对中国台湾历史地图的利用,除了整理并出版地图集,还研究其发展历史、绘制方法、图例符号,尤其是蕴含的经济、社会信息以及政治、文化意义。历史地图不仅反映人类对当时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的认知、观点和信仰,而且超越其原来的自然属性范畴,开始为当今发展提供历史背景,在大数据时代,渐成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涉及许多领域的相关理论[23,24]。本文旨在通过区别于传统舆图、以实测技术为基础的近代地图,根据文献资料和相关数据,讨论中国台湾被整体纳入清朝版图后经济社会的变迁。 2清前期的中国台湾近代地图 相对于采用山水画法、计里画方法等绘制的传统舆图,近代地图优在实测技术,有经纬线,也更精准。结合对中国近代地图的时限界定[25],清康熙五十三年(年),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os.DeMailla)等在实测台湾后所绘制的底图(以下简称“年图”),被公认为是中国台湾最早的近代地图。该图先在欧洲出版,又是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一幅,但无论中外版本,中国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均含在《福建省图》中,岛的东侧竖写“在福尔摩沙的台湾”(Tai-DuanauIsleFormose),字比西侧横排的“福建”(ProvincedeFo-Kien)要小得多,意味着中国台湾只作为Formose之小岛,是福建的辖府,位置在福建右上方(图1),而中文版本则在右下方。图的方位一改上东左北“横轴式”的惯例,变为上北下南,并以北京为0o经线,中国台湾位于3oE~5oE。其内容也十分简单:西半部海岸线、中央山脉、溪河、聚落,似乎反映中国台湾尚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 图1冯秉正所绘制的中国台湾底图(欧洲版)[1] 2.1清廷封禁,孤立东部在化外世界 年图其实只有西部半幅,中国台湾的东部压根儿没有绘出。之所以如此,冯秉正解释为,“只有大山的西部才是属于汉人的……在东部只有番人居住”[26]。换言之,此时的东半部还被视为化外或界外之地。 历经荷据、明郑时期,清领台湾之初,在弃留争论后,中国台湾被整体地纳入清朝版图,“地方既入版图,土番人民均属赤子”的观念已经确立[27],但东部仍被清廷看做“化外野番”,“其间人形兽面,鸟喙鸟嘴,鹿豕猴獐,涵淹卵育,魑魅魍魉,山妖水怪,亦时出没焉”[28]。“生番出没其中,人迹不经之地;延袤广狭,莫不测识”[29]。心理上横亘着一条防范的番界,而康熙六十一年(年)的朱一贵事件,则使心理上的番界终于变成事实,直接促成了从南到北、由土牛和壕沟构成的防御线,严禁逾越,其严重影响不仅孤立了东部,加大东西之间的不平衡,而且埋下了西方列强借口东部被划定在界外,是“无主”之地,并不断觊觎的后患。年图仅有半幅,似非冯秉正视野所限或有意为之,相反,更重要的是清廷封禁政策的具体表现。 2.2大陆居民移入,汉番并存而互动 直至18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中国台湾西部并无大规模的土地拓展,“台地当年有社无庄,南北千余里,草木茂密,各番以世相承,用资捕鹿,名曰‘草地’,此疆彼界,社番自定”[30]。其中,南路汉番间居,仅淡水(此指高屏溪)以南均为潮州客庄;中路唯斗六门以南,鹿场悉变良田,其余地方大陆移民很少到达;北路除竹堑(新竹)、新庄、万华开始拓展外,地广无人,野番出没[31]。原因在于当时虽有大陆居民大量移入,累计人数不足20万,且处在以港口为据点、或集聚建市街、或四周扩散的初始阶段。中国台湾原住民依汉化先后、聚居高低,分“熟番”“生番”或“平埔族”“高山族”,人数也近20万[32]。前者采取游耕方式,移村和易地耕作是其常态;后者以中央山脉为中心,分布在西部浅山和丘陵、中央山脉、东海岸、兰屿四区[33]。因人地矛盾并不突出,除部分沿海平原受港口据点影响而开发,多数未成为大陆移民的聚居空间,原住民仍在自己的家园。 年图足以说明此点。图上标注地名24处,除山、河合计6处外,聚落18处,其中,“xx社”有7处,自北向南依次是竹堑社、中港社、后垄社、大肚社、麻豆社、新港社、放索社,占38.9%。“社”是原住民的聚落形态,不仅大量存在,而且空间分布上具有越往北去、越靠近海岸线的特点,吻合于台湾土地拓展先由北向南、又自西往东的基本态势。 2.3少量聚落,尽显中央权力的延伸 献地图类似献江山。年图绘制于清初,是清廷对台湾实施统治的象征之一。图上“xx社”外的聚落有11处,几乎处处与行政管理、军事布防相关,凸显中央权力的延伸。鸡笼城、淡水城由明末西班牙殖民者修筑的圣萨尔瓦多(SanSalvador)、圣多明哥(SanDomingo)而来,当时除传教、贸易外,军事上有牵制荷兰殖民者的考虑,清初以“实为贩洋要路,又为台郡后门”,于台湾镇标中营拨千总一员、台协左营把总一员,每半年轮防[34];沿海港口设汛,其功能除海防外,并查验无照偷渡、私越口岸船只,有笨港汛、大湖汛、八里分;安平镇无疑是台湾行政、防御、贸易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修筑热兰遮城(Zeelandia)、普罗文蒂亚城(Provintia),统称大员(Tayouan),郑成功设置一府二县,以此作为承天府治、万年县治之所在,清初设一府三县,隶福建省,其中,台湾府、台湾县仍以此作为府治、县治之所在,而诸罗、凤山知县皆以南北路蛮荒未开,暂附府城治事,不久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分防厅,以半线为治之所在;斗六门扼南北咽喉,是进入中央山脉的要道,可见其重要性。 3清晚期的中国台湾近代地图 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实测技术后,近代地图被不断地绘制,《台湾地舆总图》是其代表,反映了中国台湾从传统走向近代之时经济社会的变迁。该图包括描述中国台湾全岛景象的《全台前后山总图》1幅和三府、十一县、三厅、一直隶州合计18幅分区图。绘者不详。绘制年代在光绪十四年(年)至光绪十七年(年)(以下简称“年图”)[35]。图的方位依上东下西的绘图惯例,但以格林威治为0o经纬线,中国台湾位于oE左右、22oN~24oN,右下角有明确的图例符号:用象形符号标注山脉、溪河,用线形符号标注道路、电报,用几何符号标注府、县、厅、州之所在(图2)。 图2全台前后山总图[35] 3.1番界渐消,中国台湾建省 通常认为,随着累计多万大陆移民的渡海入台,中国台湾经历了先由北向南、再自西往东的土地拓展,在先后聚居于西部港口、台地、近山之时,嘉道年间屡屡逾越番界,向东进入花东纵谷南北两端。由此导致番界几经变更,不断向深山延伸,甚至“土牛界禁,在乾隆年间早经奏明虚设”[36],使废止番界、纳东部入行政管理体系被提到清廷议事日程。光绪元年(年)正式废止番界,并先后设恒春县、卑南厅,当中国台湾行政管理体系南北分立,实施二府、八县、四厅时,东部大致北起苏澳、南至八瑶湾间合计多里的空间,成为其中的一部分[37]。十数年后,中国台湾与福建分治,单独建行省,并实施三府、十一县、三厅(年添设南雅厅,又作四厅)、一直隶州行政管理体系。 番界渐消,中国台湾建省,有许多内容与年图高度对应。一方面,因大陆移民土地拓展遍及多地,原住民或汉化,或迁移,仅光绪十一年(年)冬至光绪十二年(年)夏的半年内,就抚番多社、7万多人,光绪十三年(年)春夏间,后山抚番社、5万多人,前山抚番多社、3.8万多人[38],汉番间居发生逆转,图上“xx社”的标注仅社寮、水里社两处,相对于其他各色地名七八十处,占比已极低。另一方面,总图“说略”明确了西部、东部的所辖范围,“计前山自极北之基隆、宜兰交界草岭顶起,至极南之恒春县辖鹅峦鼻海口止,共计民站八百五十里;其后山南自鹅峦鼻起,至宜兰极北与基隆交界之草岭顶止,共计七百六十里”[39],而18幅分区图,除分别绘制府、县、厅、州的地表景观、地理信息外,都有“说略”,叙述各自的称呼、设置、沿革、现状、所辖及其对外联系的陆路或水路。 3.2经济重心北移,四港集聚 开埠通商,中国台湾日渐沦为西方殖民者廉价工业品倾销地和原料农产品掠夺地,其突出表现是北部的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较之于同治七年(年)至同治八年(年),光绪十九年(年)至光绪二十年(年),华货进口增加8.8倍,洋货(不含鸦片)进口增加8.6倍,茶、糖、煤、樟脑出口增加7.3倍,而且早在光绪七年(年)就已超过以米、糖为出口大宗的南部,是其2.3倍[31],意味着经济重心正由南部移向北部。受此影响,产业、人口大量集聚,虽按当时南北的分界大甲溪划分,图上北部的府、县、厅、州仅6处,占33.3%,但其聚落规模及其集聚速度超过南部。光绪元年(年),万人以上聚落8处,南北各占一半,人口数量北部超过南部6次;光绪二十五年(年),万人以上聚落数量及其南北占比不变,人口数量北部超过南部8次,平均集聚速度北部24.9%,南部9.9%(表1)。 年图以“xx港”“xx澳”等标注的地名近30处,占各色地名三分之一以上,表明港湾在台湾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仍被认知,尽管当时已有分化,或停滞衰落,如大安、海口;或改变功能,如板桥、北港;或开埠通商,快速集聚,如基隆、沪尾(淡水)、打狗(高雄)、安平,其年均贸易额合计占港口贸易总额的88.2%,而北部两港更是重中之重,合计占67.1%[42]。 3.3洋务新政,尤重内外联系 线形符号是年图颇具特色的信息之一,分虚线和实线两种。前者指道路,走势基本沿海岸线,少数地方并行数条,交叉相连;后者指电报,有陆上线路和海底线路。 中国台湾的洋务新政涉及兴路、开矿、造商船、办企业、建学堂、通电报等,图上仅反映兴路、通电报两项,可见对岛内以及向外联系的重视。兴路包括辟山路、铺铁路。前者由沈葆桢实施,分北中南三路同时开工,光绪元年(年)10月完成,合计km,初步打通中西之间联系[31];后者由丁日昌首倡,经刘铭传集资修建,光绪十七年(年)完成,从基隆至新竹,全长.7km[38]。但因台湾大规模的兴路始于年,此时尚未形成贯通的路网,图上标注似有不符实际之嫌。通电报先由沈葆桢建议,“架设台南至厦门的跨海电线及厦门至福州的陆路电线”[43],丁日昌时完成从台南至安平、旗后两条陆上线路,合计95km,刘铭传时完成从沪尾至福州长nmile、从安平至澎湖长53nmile两条海底线路,从基隆至台南长0多公里陆上线路[38]。 4日本占据时期的中国台湾近代地图 中国台湾的战略地位一直为日本所认识,获取地理信息、绘制近代地图就是未曾放松过对中国台湾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aerwaduo.com/ssswdjd/6388.html
- 上一篇文章: 十四亿人的逐辣之欢深度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