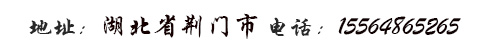拉美的孤独与我们的时代马尔克斯逝世七周年
|
今天是马尔克斯逝世7周年,年4月17日,这位拉美最伟大的文学巨匠走完了他的一生。马尔克斯的闪光点绝不只是他的文学表现,他用作品承载着整个拉丁美洲的孤独,而这份孤独又与我们的孤独相通。此刻,一些原因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 被切开的血管 整个南美洲加上北美在美国以南的区域,就是我们所称的“拉丁美洲”,在大航海之前,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们发展出了自己文明。古代这里算不上和平,一些文明还有活人献祭的传统,不过这些暴力比起拉美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商人们急切地想要和亚洲做生意以获得更多商品,当时通往亚洲的商路受到重重阻碍,但地球是圆的,朝另一个方向不是同样能到达亚洲么?于是哥伦布游说西班牙国王,组建了船队,在年向西行驶开始了寻找亚洲的航行。 两个月的航行后,他们果然发现了一片大陆,哥伦布以为这就是亚洲的印度,激动地称当地人为“印第安人”。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哥伦布找到的不是亚洲,而是美洲这片“新大陆”——尽管美洲一直在那里是一片古老的大陆,这里遍地都是黄金和白银,还有肥沃的土地和科技严重落后的人民。于是,侵略开始了。 先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这里挖矿,将每一座可能含有金矿银矿的山头挖掘得千疮百孔。当地的原住民被抓为奴隶当矿工,长期承受超负荷的劳动直至死去。16世纪大量拉美原住民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体自杀,20世纪欧美学者论证,这种集体自杀是这里原住民的基因不好有自杀倾向。 在玻利维亚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波托西,这里处处都是银矿,被发现时就震惊了整个欧洲,《堂吉诃德》结尾处“整个波托西的矿产都不够报答你的”说的就是这个富饶的代名词波托西。在17世纪,这里是世界上最大、最富有城市之一。但西班牙人把这里挖空后废弃,只留下破败的城市和上百万奴隶的尸体,直到现在,波托西的人口只有四个世纪之前的三分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在四个世纪前,蔗糖还是奢侈品,自从哥伦布把“白色金子”甘蔗从西班牙带到美洲,这里就成了为欧洲提供蔗糖的种植园,巴西东北部肥沃的土地使它成为17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产国,荷兰人受此启发,又从非洲贩进更多奴隶去东加勒比海生产。 拉美的肥沃土地种满了殖民者的经济作物,没地方种粮食了,当地人民想要吃粮食和食盐只能进口,随之而来的就是饥饿与贫困。孩子们因为无法吃到足够的食物,也缺少矿物质的摄入,本能地吃起泥土。大人们为了防止孩子啃食泥土,不得不给孩子带上牲口用的口套,或者把孩子们装进柳条筐里吊起来。而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的死亡每天都在这片土地发生。 拉美土地的富饶导致了拉美人民的贫困,终于,被压迫的人民拿起了武器,将殖民者赶走,经历了三百多年血腥剥削的拉美终于获得独立。可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又来了,将拉美独立发展的梦想扼杀在摇篮中。 英国最讨厌贸易壁垒,他们的原料来自世界各地,加工后再倾销全球,控制各地区的经济命脉,伴随着血与火,英国人将货物出口到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国家。中国被鸦片战争叩开了贸易大门,拉美也未能幸免地被英国货物攻占。英国人深知贸易壁垒的重要性,打击着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自己本土的贸易壁垒却非常高,在英国纺织业发展初期,曾出台法令——英国公民如果出口了未加工的羊毛,就要断其右手,再犯则处以绞刑。在教区的牧师如果死了,必须证明其裹尸布是英国的本国货,才允许下葬。 拉美尚在襁褓中的本土工业体系根本撑不住英国商品的疯狂倾销,很快被扼杀在了摇篮中。然后美国人又来了。软弱的巴西政府准许美国空军在蕴藏丰富资源的亚马逊平原拍照,随后,巴西两千万公顷的富饶土地被出售或强占。在哥伦比亚,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成为了当地最大的庄园主,工人们长期被剥削压迫,在年举行了数周的大罢工,让联合果品公司遭遇了巨大损失。年年底,大量罢工的工人在火车站周围被屠杀。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大规模的罢工,以及殖民者的血腥镇压与暗杀。当拉美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了当地政府,剥夺了联合果品公司的特权,将土地还给人民,美国军队却又扶植了新的军事独裁政权,重新把土地给了联合果品公司。拉美就像被困在永恒的沙漏中一样反反复复,始终挣扎在贫困与战争中。 殖民拉美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最多的事件,没有之一。据估算,约万拉美人民在被殖民过程中非正常死亡,这个死亡人数,是纳粹屠杀犹太人数量的15倍,是大西洋黑奴贸易死亡人数的9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起来的死亡人数还多。 经年累月被殖民剥削的拉美就像一段被切开的血管,直到《百年孤独》付梓,这一切仍在继续。拉丁美洲几个世纪以来的遭遇里,催生的不仅是贫困、不幸、死亡、战争,其独特而动荡的社会环境同时也生产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西方的视角下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马尔克斯,这个伟大的作家用密集的叙事、独特的讲述方法,将拉美残酷的现实压缩在了自己的作品中,震惊世界。 拉丁美洲的孤独 第一次读《百年孤独》是在高中暑假,那时觉得整个布恩迪亚家族好乱,人名乱,性关系更乱,每个人都太孤独了,整个家族各种乱伦互相折磨了上百年,所以“百年孤独”。奇怪的是,我那时听到这种文学叫“魔幻现实主义”,却不觉得有什么“魔幻”——即便出现了鬼魂、羊皮卷上的预言、乘风飞走的人、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大雨,这些当然不会在现实中存在,可这些因素根本不是书的主基调,就像《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会借东风会续命,我也根本不会用“魔幻现实”来形容《三国演义》。 大学里稍微了解一些拉美的历史,重读这本书,就发现这写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家族的孤独,而是拉丁美洲的孤独。每一个看似不寻常的事情,长着猪尾巴的畸形婴儿、吃土的小女孩丽贝卡、香蕉公司的罢工和火车站的大屠杀……这都能在真实的拉美历史、生活中有迹可循。 《百年孤独》里,罢工的香蕉公司工人们被屠杀后,火车厢里装满了尸体开向海边抛尸,一个主角侥幸没死,从火车上跳下去活了下来,回去后却发现没有人记得香蕉公司的屠杀,就像屠杀从没发生过。欧美视角下看到觉得魔幻,“死去那么多人怎么所有人都不记得这件事呢——但这就是拉美真实的社会。欧洲人不理解这种真实也就算了,我们难道也不理解么? 马尔克斯很讨厌别人把他的作品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他在领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压根没提享誉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甚至没提文学,他讲的是《拉丁美洲的孤独》,讲的是拉美的政治、经济、生活。这场演讲都不像是领奖词,而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控诉。在演讲开头,他略带调侃地说了些拉美的荒诞现状,然后语气越来越严厉,开始陈述拉美依然在遭受的苦难: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5次战争,17次政变,出现一位以上帝名义在当代拉丁美洲进行第一次种族灭绝的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便不幸死去,这个数目比西欧自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乎有12万之多……无数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里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们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为了避免此类事情不再发生,整个大陆大约有20万男女献身,其中10万多人死在中美洲3个极权主义的小国……在具有热情好客传统的智利,逃亡者多达万,占本国公民的10%。乌拉圭这个只有万人、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小国,五分之一的公民在流放中消失。萨尔瓦多内战自年起几乎每20分钟就多出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鲜活的人命,这早已超越了文学手法能展现的范围,文学写不出拉美人民生活的残酷。当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进入同一起跑线,跑赢的永远是现实,作家的想象力则微不足道。 而评论家们一个劲地夸马尔克斯想象力真好,这种褒奖更像是侮辱。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方法使别人相信他们真实的生活。 拉美人民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真实可信的必要财富,这就是拉美孤独的症结所在。 拉美人民被掠夺的不仅是生命和财富,他们的叙事也被掠夺,失去了被理解的可能性。据记载,西班牙殖民者巴尔博亚第一次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后,成为同时看到两大洋(大西洋、太平洋)的“第一人”。可是,之前居住在巴拿马的原住民都是瞎子吗?还是说,巴尔博亚这个殖民者才算人,那些原住民根本没有被看作是“人”? “为什么你们可以接受拉美在文学上的独特性,却要全盘否定我们独立自主、举步维艰的社会变革呢?”马尔克斯问出这个问题时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却不愿说的是——恰恰是西方世界对拉美文学的认可,加深了他们对拉美政治现状的实质不认可。西方世界不需要真的理解拉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更不愿意承认这是他们曾经的殖民统治造成的结果,只需要从美学和文学角度去观赏:“马尔克斯的想象力可真丰富!”然后,就已经完成了一切。 意识形态差距大的地方,人们往往会用审美来填补其中的沟壑。美苏冷战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意识形态对立最严重的时期了,但在当时,《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西方美术学院必学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在苏联国内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同时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根据托尔斯泰原著拍出的《战争与和平》在西方世界成为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不止是冷战,今天的伊朗电影在全世界大放异彩被人称赞,但伊朗的政治体制却总被抨击。我更想举的是一些大家身边更熟悉的例子,但是无法讲出来了,只能绕一大圈。 不管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对立,背后属于赤裸生命的情感总有共通之处。美的表达本来可以构建人与人互相沟通理解的桥梁,但现实中却往往成了一条可耻的避难所,人们只愿意活在自己狭隘的世界中,对另一种生活下的人,最多只愿意从审美角度理解,将那些真实存在的生活叙事当作一段想象力丰富的故事、一场猎奇的表演,在美学上完成了一切评判,而拒绝理解对方真实的生活。 而真正让人难过的是,大部分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高高在上隔岸观火,可以观赏别人从苦难叙事里绽放出莲花。而现实中的不幸与灾难往往是随即降临的,每个人都可能莫名其妙就结构性地成为了“魔幻现实”里的角色——用哲学家阿甘本的话说——成为了“神圣人”。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泛审美化的关怀被扩展到越来越多人身上,人们通过小说、电影、媒体认可他们的“故事”,看了《百年孤独》就敬佩拉美,给《寄生虫》搬个奥斯卡奖就反思了底层小人物的悲惨经历,看几个故事就像买了赎罪券。但与此同时,苦难的人只能被美学捕获、征用,被迫将自己的苦难叙事献给全社会成为共同的叙事财富,那些不能成为叙事财富的真实也就不再会被理解。 用他人的尺度来解释我们的现实,用我们的尺度解释他人的现实,都只会让我们像走廊上的马一般无法调头,然后每个人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 马尔克斯的孤独,又何止是拉丁美洲的孤独呢? 我们的时代 (本节无内容。)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往期相关推荐: 盗取美学规律的人 17岁跳桥身亡的少年——赤裸生命 故事的消失就是唯一的故事 卡夫卡的城堡 神秘的大人物 乘桴您的手指可以点石成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saerwaduo.com/ssswdfj/8898.html
- 上一篇文章: 他的油画作品独特有力,充满美感
- 下一篇文章: 柳暗花明摄影师的城市鹿地放映